讲座报道丨张艳梅:新世纪文学中的城市形象
日期:2019-07-10 来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新世纪文学中的城市形象
编者按:2019年6月29日,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联合邀请张艳梅老师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市民朋友们做了一场题为“新世纪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的讲座。

精彩演讲内容回顾:
一、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学
我们每天生活在城市之中,熟悉城市的表情、气息、声响、节奏和色调,也熟悉城市脉搏里偶尔的停顿、凝滞、低徊和感伤。悲欢离合,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每个城市有其独特的气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载体,也是心灵和情感的居所。
对大多数人而言,能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外表、秩序、规则以及发展水平,城市的心灵与灵魂难以触及,然而从城市的外在表现也能看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扩张的空间感,不断加速的时间感,同时也带来了压迫感和焦虑感。近几年流行的两个词,“丧文化”与“佛系文化”,其实就是对于焦虑的一种逃避,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段子的方式去排遣这种焦虑感。
如何看待城市的发展,原住民,外来者,观光客,从不同角度看待城市的发展,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差异。随着自己视野的改变,自身的内心感受与理性表达也会发生变化。认同感建立在身份自觉基础上,而外来者往往有着潜在的认同危机,多少会有一些缺失感、不适感和疏离感。从一个陌生的外来人口,逐渐融入城市,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对城市的认同感,是对一个城市不断了解,不断融入,需要一定时间的过程。
每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独一无二的文化品格,不同的城市会给人留下不同的文化印象。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城市书写是带着问题意识的观察与思考。
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介绍了北京城与京味文化,北京作家,包括文化的分裂与多元,文化的眷恋与批判,也包括城市文化标签,文化符码的形成等。理解一座城市,首先看到的是其代表性建筑,其后是建筑背后的城市文化。
杨东平的《城市季风》详细梳理了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表现,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这本书出版之后,形成了突破国家观念笼罩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如沪港双城,台北与北京,北上广三城等比较研究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这些研究既有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也有美学、伦理学、历史学研究视角,这些研究对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城市里的特色食物,也是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比如《舌尖上的中国》的制作,其唤醒的是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回忆,说到早茶便想起广东,提起狗不理包子便想到天津,还有北京、南京、成都、武汉等地的特色饮食。
在既有观念中,城市是喧嚣、物质的,而乡村是宁静、自然的。作家在书写城市与乡村时,并不会一直秉承着这样的文化理念,在其作品中,城市与乡村是处于变化中的,这种变动不居,不仅体现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能力,而且也是文学与生活相呼应的例证。在当代作家作品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果说现代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就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城市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表征,我们置身于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在传统文学中,乡村是“世外桃源”,但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征地、拆迁、留守、污染等社会问题也有体现,而正因为现实性的表达,对于生活的理解才更加丰富多元。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作家们的作品往往带着对城市文明的反思,既写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也包括对乡土文明的眷恋,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1980年代中期,处于一个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文化的西化与寻根之间的对话是这个时期的主流;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文精神讨论成为主流,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型过程是一个理想主义到世俗主义的过渡,作家们在作品不断追问人文精神的失落带来的严重后果。21世纪初,开启了“底层写作”的文学思潮,部分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公平,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体现了作家们人文情怀和对社会发展的思考:人究竟为什么活着,我们去追求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就文学而言,显然包含着对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启蒙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公共话语空间,作家们是希望给人文精神留下更多坚实土壤和自由度的。
从城市文学发展而言,作家们不仅通过文学创作展现出一个城市的人文景观,还包括城市的形象与生活空间。如叶兆言的南京,陆文夫的苏州,冯骥才的天津,慕容雪村的成都,池莉的武汉,包括后面我们要聊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城市生活的整体,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城市生活中的心理情感空间,承载着隐形的多重体验与复杂情感,如林秀赫的小说《五福女孩》,通过主人公成长过程,那一条街道,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又像是一个无限延展的时间黑洞,女孩从出生,到成长,读书,恋爱,封存的记忆,坠落的雨滴,无法打开的心结,是广阔宇宙里极其细微的附着点,也是人类自身难以超越的困境隐喻。小说重在揭示人们如何走出自己的世界,又能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还有一些作品突出表现城市外来者的不适感,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主人公涂自强的成长经历作为主线,体现了年轻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如何立足以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城市生活既有柴米油盐的日常性,又被作家在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赋予了隐喻和象征性。在作家笔下,如何更加丰富地呈现出城市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对人的生存进行哲学反思,还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去呈现人的生存的荒诞性,一个作品能够感染人们,都是因为作家是以人文情怀和对待现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起点。
二、新世纪文学中的城市形象
(一)北京:惟有王城最堪隐
1. 京味市民小说的前世今生
第一代京味市民小说代表作家是老舍先生,他的《四世同堂》,到《茶馆》,再到《正红旗下》,用纯正的京腔京韵和特有的幽默呈现了北京四合院里的日常生活。
第二代京味市民小说代表之一邓咏梅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市井生活,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交融,包括像《烟壶》以具有民间性的器物,风俗画的形态,表现文化的传承与记忆。同时期的还有刘心武的《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表达了文革后北京城的新变化。
第三代京味市民小说,相对更为人所知的作家是王朔,作为一个红色时代的遗民,王朔用解构和话语狂欢的方式塑造了一群顽主形象,这些多余人形象带有反文化、反智、反精英价值观的冲击,成为当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王朔京味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调侃,调侃政治,调侃爱情,调侃一切,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可被破坏的。
2. 徐则臣:京漂与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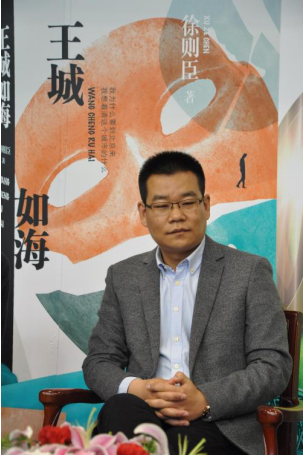
徐则臣作品包括花街和京漂两大系列。京漂系列体现了一群漂在北京,活得相对失败的年轻人的生活及情感状态,写出了京漂一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焦虑。包括《跑步穿过中关村》《伪证制造者》《居延》《轮子是圆的》等。徐则臣说,“写作本身就是在建构我一个人意义上的乌托邦。”在《如果大雪封门》中,通过几个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展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是“我”,行健,米箩这些外来的年轻人如何在这座城市扎根,另一方面是林慧聪这样的年轻人怀着梦想而来,保有纯洁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却不断遭受挫折。小说中的大雪封门寄寓了一个理想世界,天空中飞过的鸽子代表自由。
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设置了花街、北京、耶路撒冷三个地域空间,其思想轨迹既是回望百年,向鲁迅的《故乡》致敬,又是“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史。北京连接故乡和世界,是生命起点的投射,也是通往未来的道路。通过空间拓展,将读者带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思考人生的理想形态。
还有基于“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王城如海》,书写精英、大学生、保姆、快递员等各个阶层眼中的 “新北京”。小说通过海归话剧导演余松坡在话剧《城市启示录》中的言论,引起年轻人不满,引发公共事件,由此展开城市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问题。驱霾神器,梦游症,二泉映月,各种象征物综合构成了一个整体隐喻。一个历史的拷问,一代人精神上的病态,小说以现实主义的表达抵达了象征主义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城市书写。
徐则臣最新长篇小说《北上》,通过两个时代,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以及命运的起承转合,书写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民族的旧邦新命,是徐则臣对于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3. 叶广芩:跨越时空的怀旧

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以漂泊者为主,表达了外来者与北京原住民的交融,而在叶广岑笔下,更多的是遗老的生活。
《豆汁记》通过描写一个普通女性莫姜一生之中的起起落落,这个女人的软弱善良,以德报怨,在每一次变故之中,每个人的取舍,描绘北京人的性格特征,书写在叶广岑眼中的老北京味。叶广岑的小说通常用微观视角呈现丰富的日常生活,叙事平和、通达,节奏舒缓、从容。她写北京城百年的人物众生相,写北京市民的生活观念、北京社会的风土人情,就像那一碗豆汁,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味道,叶广芩,为我们用文字保留了古都北京特有的文化底蕴。
北京是一座有着千年文明积淀的古城,其城市文化更接近传统文化,相比较而言,上海的城市文化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
(二)上海:你看那众声喧哗
上海作家的作品中,带有着沪言沪语的特色,与北京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官印象。
1. 海派文学的千回百转
海派文学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鸳鸯蝴蝶派流行时期属于海派市民小说的滥觞阶段,上承《红楼梦》、《花月痕》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感伤的影响,展现出一种落魄者的孤独感。
第二阶段是30年代新感觉派,带来的是旧上海30年代声光电影般的城市形象,同时描绘出标志性人文景观与生活方式;同期还有一些左翼作家,如茅盾的《子夜》,以一种理性社会剖析视角去呈现30年代大上海波云诡谲的时代风云。
第三个阶段是40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代表人物是徐訏、无名氏、苏青、张爱玲等,他们把宏大的家国情怀和上流社会目光转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比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多取沪港双城,表现饮食男女日常悲欢,写她对于生命、爱情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市民文学进入衰落期,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又重回人们视野。王安忆、陈丹燕、唐颖、王宏图、张生、滕肖澜、小白等作家,从不同视角进入城市生活,以不同的身心体验带给我们都市的心跳与呼吸,为读者塑造了他们各自眼中的上海形象。
2. 王安忆:一个人与一座城

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一生来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跌宕起伏,一个人是一座城的缩影。她的《众声喧哗》通过三个人的因缘际会,呈现了三种文化的交融,构成了大上海众声喧哗的一个场景。喧嚣众生,有新上海中的旧人,也有旧时代中的新人。王安忆对中国社会结构、现实路径的认知,枝枝蔓蔓的理性里多少含着反讽,她不去追踪大上海的飞速向前、新气象,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让她不能释怀,那种隐约的历史追问和现实质疑,不坚韧,却自有一份宏阔的纵深感。
上海成就了王安忆,她也成就了上海文学。
3. 金宇澄:岁月如繁花似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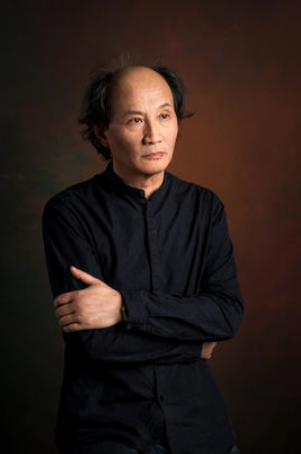
作家出发点和审美表现形式的不同,作品给人带来的阅读感受也会有差别。金宇澄的《繁花》细腻地描绘出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史。60年代少年旧梦人间烟火,90年代物质喧嚣,繁花落尽,又是新生。一座城池,一段人与人的纠葛,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小说中的语言方式以沪地方言为主,正是这种语言的陌生感带来了审美的距离感,让读者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上海。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在飞速前进的同时,有些东西是凝固不动的,在变与不变之中去了解、认识一座城市,文学是一个捷径。我们一面怀旧,一面患上了严重的健忘症。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都市症候,覆盖了心灵的繁花如梦,我们在浦东的高速发展中体验到了科幻感,这种超越时空局限的震惊感和眩晕症,也正是作家们书写城市的某种心理动因。
(三)深圳:灵魂依旧净尘山
1. 深圳文学的消费景观与精神突围
新城市或许缺少时光积淀和岁月磨砺,但这样的城市会给人以一种年轻的朝气和新鲜的活力,深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深圳是一座充满青春感的城市,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带来许多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又被期望着在人文方面带给人以精神的享受。就像人们享受着科技的便利,同时怀念着童年,渴望着绿水青山。
我们经常说起这个时代文学不断边缘化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力量、意义和价值到底如何体现?网络小说、短视频、段子手,智能AI的写作,都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冲击,文学在消费性社会,不得不面对被异化和弱化的现实,突围的路径其实还是最基本的两个支点,人与生活,写出人的存在与灵魂,写出生活的本质与关怀。
2. 邓一光:打工群体的生存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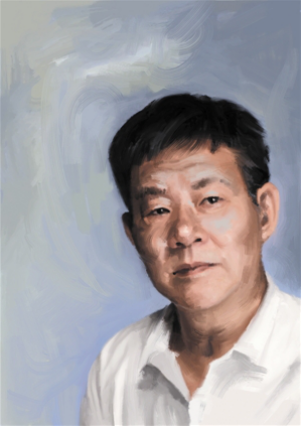
邓一光用十年时间,写下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呼吸、律动、喜悦和疼痛,既写出了高速发展的一面,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的挣扎。底层关怀在当代作家笔下,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的介入以及人性的透视。陈应松,刘庆邦,王祥夫,罗伟章,曹征路等作家,从不同视角观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以不同题材和风格的小说作品,拓展了我们社会认知和文学理解的视域。
在邓一光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深圳的标志性景观,包括莲花山、市民中心、万象城、红树林、罗湖、仙湖、前海、梧桐山、关外等等,他不是刻意把故事放置在这些空间里,而是在这样特定的时空中,去把握深圳这座城市的脉搏,《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宝贝我们去北大》《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等作品,既写出了深圳的城市气息,明亮的朝气蓬勃的那一面;也写出了打工者艰辛困苦的现实处境,包括情感、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各种困境。把邓一光的作品连缀起来,就是一部他对深圳的认知史。
3. 蔡东:知识分子的城市反思

蔡东小说大多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创作,在她的笔下,很多主人公都有着一个自救与救赎的努力过程。近期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天元》《照夜白》《伶仃》等作品中,无论是大学老师和电台播音员对滔滔不绝的厌倦,还是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失智教授,抑或是拒绝狼文化渴望慢生活的海归精英,还有婚姻失败从逃避到面对的中年沧桑,都从不同视角隐喻了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临着的精神遭遇。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哪类人,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对于蔡东而言,都是试图带领着读者解开都市人生的心结,找到生活失败的症结,找回失落的、出离的自我。
面对喧嚣的种种,蔡东亦能沉下心来,有沉思的能力和耐力,能思及问题根本。她的写作能力体现在,面对日常题材时总是能再进一步,再深一层。她还懂得运用智性和诗性的力量,借此减轻现实的重量,摆脱现实的限制,让人物身上那些黏稠的泥淖逐渐风干,一一脱落。
还有一批书写深圳的年轻作家活跃在中国文坛,包括丁力、吴君、毕亮等人,将深圳形象带给读者,他们具有这座城市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一面,同时也在不断探寻复杂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始终怀着文学的责任感,不断追问生活,表达对人与社会的关怀。
无论是哪一种城市形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在享受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除了带来生活便利之外,还带来更多精神文化追求的可能性,例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美术馆、音乐厅、茶馆、咖啡馆等,提供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使人们拥有了一种更高的文化认知和文化体验。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我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基于智能生活的愿景,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5G、智慧交通等等,期待实现智慧人居生态。这种智能化生活对文学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关话题,值得大家一起探讨。
城市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恶托邦,时代的裂变、人心的裂变,价值观的裂变是人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新人类与旧世界,大时代与微生活,不断被消费性挤占的公共空间,不断被意识形态渗透的私人空间,群体的道德考验与个体的精神隐疾,全球化与地域性,无论从知识体系建构,还是文化、心理、情感层面,每一代人的体验、思考和记录,呈现在作家笔下,这些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千与千寻》结尾,千寻问:我要一直走吗?白龙答:是的,别回头。千寻又问:那我们还会再相遇吗?白龙点头:会的。希望在寻找自我的路上,我们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能够和更好的时代、更好的彼此再次相遇。


